男女主角分别是宋栀陈易的其他类型小说《生娃后和离:夫人你为何这样宋栀陈易 全集》,由网络作家“三鲜馅儿”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第二天早上,陈易才披上外衫,宋栀就醒了。他本想说时间还早,可以再睡会儿,却见宋栀眸子很亮,可见是一点不困,全是要归家的兴奋。陈易笑了下,趿拉着鞋去桌上倒了杯温水。宋栀也是个被伺候惯的,杯子都凑到嘴边了,哪有不喝的道理。陈易给倒的又怎么样。炭盆后半夜才熄,烤的她嗓子要冒烟,就着陈易的手,宋栀咕咚咕咚喝了两杯水。“你先穿衣裳。”陈易把床尾的棉衣拿到宋栀眼前,才出门去打洗脸水。怕开门的冷风扑着宋栀,还把床帐合了个严严实实。宋栀撇了下嘴,没忍住说了句粗话,“孩子死了你知道来奶了”,也不纠结,快速动手穿衣。王氏早都醒了,正把昨晚几块剩下的没肉鸡架子倒进锅里,准备添点水煮个面条,然后再打两个鸡蛋进去。上河村离安阳县远些,牛车得晃悠一个半时辰,大...
《生娃后和离:夫人你为何这样宋栀陈易 全集》精彩片段
第二天早上,陈易才披上外衫,宋栀就醒了。
他本想说时间还早,可以再睡会儿,却见宋栀眸子很亮,可见是一点不困,全是要归家的兴奋。
陈易笑了下,趿拉着鞋去桌上倒了杯温水。
宋栀也是个被伺候惯的,杯子都凑到嘴边了,哪有不喝的道理。陈易给倒的又怎么样。
炭盆后半夜才熄,烤的她嗓子要冒烟,就着陈易的手,宋栀咕咚咕咚喝了两杯水。
“你先穿衣裳。”陈易把床尾的棉衣拿到宋栀眼前,才出门去打洗脸水。怕开门的冷风扑着宋栀,还把床帐合了个严严实实。
宋栀撇了下嘴,没忍住说了句粗话,“孩子死了你知道来奶了”,也不纠结,快速动手穿衣。
王氏早都醒了,正把昨晚几块剩下的没肉鸡架子倒进锅里,准备添点水煮个面条,然后再打两个鸡蛋进去。
上河村离安阳县远些,牛车得晃悠一个半时辰,大清早的还冷,肚里没点热乎东西可不行。
唉,鸡蛋。
她就两只母鸡,一只母鸡一天下一个鸡蛋。她这嘴怎么就这么快,亲家还能缺只鸡?小花鸡年纪小些,那就捆上小红鸡/吧。王氏纠结又迅速地做出了这个重大决定。
村里有牛车的那户人家姓冯,陈老汉早就和他说好早些来家门口接人。陈易和宋栀夫妻俩吃完饭,收拾好东西,赵老汉正好赶着牛车过来了。
上河村到安阳县,车费是一人八文,现在农忙,正是用牛的时候,一人本应多加两文钱。不过自春节后,村里就没几个人去县城里,正有需要出门采买或透气的村民,一辆牛车倒是装了个满满当当,就还是按了原价。
赵老汉人情练达,先去了别的要去县里的人家,把他们挨个叫醒,又给留下两个舒服点的位置,才赶牛车去陈家接人。
曹家的不服气,意思一样的钱人家就能坐好位置?
赵老汉也不恼,回:“要不你也多付三文钱?”
上河村离安阳县实在是远,八文钱的车费就够肉痛的了,还多付?浑身的骨头才几两重?
曹家的白了赵老汉一眼,心里骂陈家两个老的冤大头,儿媳妇罢了,当小姐的时候再金贵,嫁过来了还不是随着夫家拿捏?当菩萨供着,小心人家真摆菩萨的谱!
赵老汉见了陈易便热情招呼,“秀才公这是要去拜岳丈啊!”
陈易拱手,带着推辞之意,“您还是叫我陈老三,哪敢称秀才公。”
赵老汉心里头舒坦,牛鞭指了下空位,“快上车吧,咱们这就走了。”
陈易应着,才伸手要扶宋栀上车,就看到她狠狠舒一口气,像是下了某种决心。她突然冲背篓伸手,抓着鸡翅膀,把鸡塞进了母亲怀里,一气呵成。
“它还得给我下蛋呢。”说完,头也不回,搭着陈易的胳膊就上了牛车。又看着陈易道:“愣着干嘛,上车啊!”
陈易上车后把准备好的棉花垫子给宋栀铺好,两人坐稳后,赵老汉手中的牛鞭挥动一下,牛车便往前走了。
王氏反应过来,往前追了两步。她的手正好夹在鸡腿之间,莫名有股热/流。王氏气得跳脚,拎着鸡翅膀把鸡往前伸,“哎呦!这死鸡!”
牛车上,陈易拿过宋栀手里的帕子,低头仔细给她擦手,低声道:“你胆子还挺大。”
男人/体热,手一握过来就像是冒热气,宋栀没躲,由着他擦手指。听见陈易的话后,她本来不想回,偏不知哪根脑筋搭错了,没头没脑说了句:“鸡翅膀下面还挺热乎。”
陈易笑出了声,眼神宠溺地看她。
果真就得到了自家夫人的一记白眼。
真真是个好别扭的小女子,做好事也不许人夸。
小两口的互动被对面坐着的两个妇人尽收眼底,她们是心眼好的,相视一笑后也不再盯着看。
曹家的故意早上晚起,为着去县城里吃热乎包子,这会儿被颠簸的十分难受,也没力气说讨人厌的话。
一路相安,牛车赶在午前,拐进了行正巷。
近乡情怯,原来的兴奋高兴被紧张压过,宋栀抓住陈易的手,“叫赵叔把车停下吧。”
手上力气重,陈易叫停了牛车。
“吁!”
牛车在巷口停下,待陈易和宋栀站稳,赵老汉才问,“可还用我来接?”
不等陈易说话,宋栀就拽着陈易衣袖,“我能多留些时间吗?”
陈易怎么会不答应。
宋家门房的眼睛灵,在陈易他们下车的时候就认出了人,忙跨过门槛,对宋管家道:“小姐和姑爷到了!”
宋管家敲了下门房脑袋,“还不去告诉老爷和夫人!”
这是让他讨个巧,门房傻笑了下,绕过影壁就开始喊:“小姐到了!姑爷到了!”
今日是女儿回门的大日子,宋母一早起来后,就扎在厨房里,又怕枣泥山药糕不够甜,又怕鸽子汤过了火候,直让宋父找不见人。还是她自己约莫着时间,女儿女婿要到了,才去了前院。
刚开始宋父还笑话宋母,说什么女儿胃口从来就小,用得着做那么多菜?可左等右等不见人后,宋父就开始坐立难安,在正堂里走来走去。
宋母被他晃的眼晕,“没到时辰呢,你快坐下吧!”
“上河村是远了点。”宋父有些不高兴。
“呵,还不是你让女儿嫁......”
话还没说完,就听见了喊叫声,夫妇俩神色一喜,霍地起身,往门口去了。
宋栀才上台阶,还没和宋伯说句话,宋父和宋母就出现在她面前。
健康的完整的父亲,美丽的幸福的母亲。
一直压抑着的情绪再也收不住,宋栀提着裙子快走两步,眼泪砸到地上,带着哭腔:“爹!娘!”
不知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莫说宋家二老,便是陈易都觉出来了。
他有些手足无措,想去扶几乎跪在地上的妻子,却插不上手。
宋母眼泪扑簌簌地掉,宋父抹了下眼眶,把难受咽回肚里,说:“像什么样子,先进门。”
宋栀的贴身丫鬟翡翠也哭,宋母身边的吴妈妈也哭,但总还能听见宋老爷的话,一人一个,把母女俩连扶带抱的弄进了家里。
宋栀坐在矮凳上,一手揽着陈宛,姑嫂俩亲亲热热的一起吃完了那颗鸡蛋。
醒得晚,心里还想着事情,人就不觉得肚子饿,可半个鸡蛋进肚后,突然就有了饥饿感,还是很凶猛的那种,咕噜咕噜声震天响。
陈宛小手捂嘴笑,指着锅里,“有山药馒头。”
“这两天娘都做了山药馒头。”王氏厨艺不精,面食倒是做得不错。山药捣成泥混上面粉再撒上一把白糖,加水和成面团分剂子,上火蒸好后白生生的,绵软又清甜。
这种好东西,哪能天天吃。可她这两日,确实是天天吃。
于是宋栀忍不住想,这不会是特意做给她吃的吧。
前世她刚嫁过来时,觉得夫家穷困就算了,菜品还难以下咽,也就能吃两个山药馒头了。
她自怜自艾,并不与陈家人多亲近,现在不过主动出屋和陈宛说了几句话,便知晓了一些她忽略掉的事。
宋栀没去掀锅盖,她有点不好意思,而是转身回到东屋,捧出了个小木盒。
木盒上下两层,每层又分成了两个格子,上层是红枣和剥好的核桃仁,下层是用桃肉和杏肉做的蜜饯。
宋栀一边给陈宛手里塞了块桃脯,问她:“嫂子中午做饭好不好?”
陈宛不答好也不答不好,反而问了句:“您会吗?”
宋栀一听,就知道她那婆母肯定没少在背后说她闲话。惫懒娇气什么的,不用猜都知道。
“何止是会,给你炖鸡吃。”宋栀生气,她不会,婆母难道会不成?一瓮咸菜都能腌到发苦。
也不光是为争一口气让婆母刮目相看什么的。
她自己也有些馋了,而且还有些心虚,一锅鸡抵山药馒头,她才不想欠下什么。
想好就干。
新妇不好独自出门,宋栀在陈宛耳边说了两句。小姑娘一溜烟儿跑出家,没一会儿就领了个十岁出头的小姑娘进来。
女孩儿姓吴,父母双亡,和哥哥逃荒到了上河村。到此未满五年,还分不了田地,主要靠着吴家小子进城做工和打猎换钱为生。
家养的母鸡自然最好,可才过了年,整个村里也不会有一只不下蛋的母鸡。
宋栀也是碰碰运气。
听了宋栀的意思,吴家小妹眼睛锃亮,“我去追我哥哥!”
过了能有两刻钟,吴家小妹背着个背篓进院,陈宛机灵,赶紧把人推进屋里,门也关了个严严实实。
“鸡腿,不给石头他们。”石头是二房的小儿子。
宋栀笑出了声,吴家小妹也抿起嘴。
宋栀和陈宛往竹篓里看,两只比男人巴掌大些的收拾干净的野鸡,还有五颗青灰色的蛋。
吴家小妹很腼腆,小声说:“哥哥说野鸡卖给您省了脚力,野鸡蛋是送给您的。”
倒是懂事,还鸡毛肚肠收拾干净了,不然她真不知如何下手。
宋栀笑了下,数给吴家小妹四十个铜板的同时还塞给她一把红枣和蜜饯。
吴家小妹推辞,宋栀又说:“还麻烦你带着小碗儿去村尾买块豆腐,家里还有几把咸菜。”
野鸡不好熟,爆炒味道大不说她也不太会,不如炖汤,一下午的时间,小火慢慢煨着,晚上关门喝汤吃肉。
中午的话,后院韭菜才割过一茬,也还算鲜嫩,和用猪油摊的鸡蛋一起炒;芥菜咸菜咸的发苦,用水冲一冲泡一泡和豆腐一起煨也是正好。
这么快就想出菜色,宋栀都被自己小惊了下,随即就笑了出来。
自知道她要嫁到乡下,母亲一边叹息一边对她进行紧急教学,从点燃灶眼到简单的烹炒,要想美味复杂不可能,总能摆上几道菜上桌就是了,就这样,母亲也担心她做不来灶间的活计。
现在这般,母亲应该能放心了。
还有父亲,重活一世,她一定要救下父亲,保住宋家家财。
火苗渐大,窜出火舌,烤得脸发热发红。
宋栀往锅里添了瓢水,刷干净锅后,放猪油,倒入打散的蛋液。
两个菜弄好后放到锅里隔水温着,就叫陈宛搬出来两个小凳放在檐下。
四月的天,外面比屋里头暖和多了。
王氏从田里回来赶回家做饭时,看到的便是这样的场景。
阳光下头,一个红衣美人手里拿着绣棚,一个绿衣女童则在旁边坐得端正。红衣美人绣几针停一停和女童说话,女童的小脑袋则离绣棚越来越近。
做了祖母的女人也是女人,这样美好的场景让王氏不禁咧开嘴。
可霸道的菜饭香味,一闻就知道得放了整整一勺猪油炒菜!
她急急往前走几步又停下,可是味道真香,吭哧干了一上午地里活,本就又累又饿,这可把她的馋虫都勾了出来。
这下好了,别说骂儿媳妇不懂持家,便是冲着她板起脸都有点困难。
不用动手就有得吃,还说什么挑什么?
“娘!”陈宛跑了几步,抱住王氏大腿。
王氏接住陈宛,低头看了眼便抬头看向起身向她行礼的儿媳妇。
乡下人不讲究行礼这些,好看赖看却是能分得出来。王氏觉得她儿媳妇和她行礼的模样,像极了小儿子中了秀才后,给自己磕头行大礼的模样。
实在是说不出的好看。
这念头冒出来的同时,没顾上说话,王氏又刷地低头看陈宛。
她就觉得刚刚被什么晃了眼!
这下看清了,原来是两朵黄金丁香戴在她小女儿的耳朵上,闪闪发光。
陈宛太小了,只懂吃喝不识金银,显然没把这个放在心上。
她又抬头看宋栀,见她神色自若,得,这小儿媳更不会把这点东西放在眼里了。
穿新衣戴首饰的小女孩儿也实在好看的紧。
王氏叹气,往水缸边走了过去。
宋栀一直在观察王氏的神态动作,挑了下眉。
不早起侍奉婆母的事,就这么过了?前世可念叨了她一辈子。
王氏不冲她来,她也愿意暂时做个好儿媳妇。宋栀快走两步,拿起葫芦瓢舀了水。
王氏顿了下,还是把手伸到了葫芦瓢下头。细小的水流缓缓浇到手上,混着泥溅到地上,有泥点子蹦到她的裤腿上。
新媳妇穿得可是新衣裳。想到这,王氏赶紧把胳膊往前伸了伸。
“怎么给小碗儿这么贵重的首饰。”她还是没忍住。
宋栀回道:“我喜欢小碗儿。”
然后呢?
没了?
王氏没等到下一句。
她动动嘴,说:“知道你有嫁妆,手指缝也不能这么松。”喜欢谁就给谁金子,这叫什么道理?
“小碗儿是妹妹。”又不是外人。
......那倒也是。
但这是金子啊,哪怕只有那么一小点点,也是金子啊。
王氏没再说话。
她说啥,别说宋家财大气粗,一个县太爷给说媒的儿媳妇,她还能管住不成?
总归是没像昨天似的睡到晌午,家里一应不管的,至少今天还给做了饭。
儿媳妇嘛,一日好过一日就行,就说大房二房那两个,相处了十年八载的,不也还是作妖闹分家?
哼,她们回家可吃不上现成的饭。王氏心情突然好了起来。
不多时,陈家人尽数归家。
王氏靠在门边冲陈老汉和陈易喊:“阿栀给做了晌午饭,这下你们爷俩儿可有口福了!”
“有人给做饭就是好,我也是享了儿媳妇的福!”这句话特大声,指向性特明显。
陈家大嫂赶紧进了屋,陈家二嫂的脸黑得像铁锹头。
隔壁刘家大娘是个爱凑热闹的好心人,大声捧了一句:“你可真有福气啊!”
王氏神清气爽,年前分家的郁气终于去了干净。
完成宋母交代的任务,宋栀就迫不及待离开,但也没把陈易一个醉酒之人扔在屋里,而是叫了前院的一个小厮守着他。
宋栀舍不得母亲,宋母也好像还有千百句话要交代的,母女俩便一同去了后院宋栀的小院里。
母女俩没睡觉,也睡不着,最多再待两个时辰,用来睡觉实在是浪费。
宋母想了想,问宋栀要不要洗个澡。
宋栀本来没想的,听到洗澡两个字后,头皮发麻身体发软,仿佛已经置身于热水中了。她兴致勃勃,喊人备水:“翡翠!”
出嫁前宋母边亲手给女儿洗了头发,当时她心情复杂,一边欣慰她竟真把一个两个手掌长的小人儿养成了这么齐整漂亮的大姑娘,一遍难过女儿嫁人,还嫁到了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穷秀才家。
她当时还想呢,谁知道下次再给女儿洗澡洗头是什么时候,结果下一次来得这样快,满打满算也就三天。
“你也不要随着女婿,身体吃不消要同他讲。”
宋栀坐在木桶里,氤氲的水汽的漂浮的花瓣遮挡了大半娇躯,身前的红痕清晰。
人舒服起来,也不知羞了,宋栀抹了把滴汗的下巴,点点头。
“娘,说起来,你不觉得今年的春夏也得时间短吗?”
宋栀状似无意,似乎是因为热水澡联想到的,“我记得前年这个时候我因为热洗凉水澡叫你骂来着。”
“你还挺记仇!”
宋栀哼了声,“还说着凉流鼻涕什么的,结果我根本没事儿。但是你看现在,我总觉得冷。”
“昨儿我给做午饭,用韭菜炒了鸡蛋,听婆母说韭菜才割过一茬。”
她说着转头去看母亲神色,见她果真若有所思,“娘,我记得之前爹爹说要去蜀地瞧蜀锦,听闻蜀地闷热,蜀锦是不是很薄啊?要是像去年一样,薄衣服才能穿几天?”
“傻孩子,蜀锦不薄,算厚的,春秋穿正好......”宋母不再说话。
去年天气和往年不同,春天来得晚,没过几日却进入盛夏,夏日炎炎,似乎比以往的夏天更难捱。夏天一过,秋天也没持续多久,第一场雪很快就落了。宋母全都想起来了,去年秋霜下得早,周边村镇的居民几乎是日夜不停,才把庄稼都收完。
比起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人是很习惯高枕无忧的。对于成熟环境产生变化的感知,说迟钝也不迟钝。不迟钝体现在他们可以迅速发现不同,从而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迟钝则体现在他们相信环境的成熟度,觉得一次的变化只是意外。
可宋栀清楚地记得,这次天气的变化其实是循序渐进的,进而持续了很久很久,久到元朔二十五年的时候,陕西的黄河段久不开化,两岸百姓恐无水浇灌田地。
事关温饱,恐慌是压也压不住,也是因为这个,当年陈易才定了官位,没到走马上任的时候呢,就总是在户部一待一整天。
宋母看着玩水的女儿,若有所思。他们不务农事,没能把一切结合起来看。
“那你觉得春衣料子可要少进些?”宋母心中已经有了盘算,不过女儿名下有间绸缎铺子,还有两间布庄,便有心考校一番。
天气多变,具体的她也记不清,思考片刻道:“绸缎庄子倒是不用有什么变化,富贵人家一到了季节都换衣裳,两套四套的都有定数。布庄少进两成吧。”
“两成?”
“布庄面向普通百姓,春秋衣裳本就能互相穿着,冷的话里头加件保暖的细布衣裳就行。每年大批进货春衣料子的时候,进价定下来多少年了,一匹布上下差不到十文钱,就算春天卖出去不到一半,堆放到秋天再卖,应该不会有损失。”
宋栀觉得,冬天才是挣钱的好时候呢:“比起蜀锦那金贵东西,不如叫爹往山东和陕西多走走,买些田地好好种棉花。”
“要我说绸缎这东西就是看个漂亮,不如太/祖爷实在......”
宋母赶紧把女儿叭叭不停的小嘴给堵上,“你可真是什么都敢说。”
大邺的开国君主太/祖爷为了休养生息,也出于重视民生的角度,在稻米小麦之外,还鼓励百姓种植棉花,到了太/祖爷驾崩的时候,三十五年后,大邺的百姓吃饱穿暖已成普遍。
可能都是一个过程,中间两个皇帝也没有更改国策之意,直到现在。
元朔帝嘛,是个贪于享乐的。明面上不违逆祖宗之意,可上行下效,自有人为了哄他高兴顺着他的心意做事。
就看她爹,不也一心往绸缎这华而不实的东西上费心钻营。蜀锦紧供着皇族贵人们使用,余留下的那一点又不知被分成多少个份额散落在各地富商手里,费老大劲,能弄来多少?
已经有些不计成本的样子。
宋栀眼珠子乱转,“有时候做生意也是烦,当个大地主也挺好,只管收租!”
这是认真分析了两句又开始不认真了,但宋母已经觉得满意了,“蜀地其实也是不好进,我也担心你爹,也四十多岁了。”
宋栀赶紧点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呀!”
她东扯西扯,为了宋家生意不假,更多的就是为了不让她爹入蜀,还没等她顺其自然说得再明白点,她娘就上道了。
前世宋父就是死于蜀地,官府调查后按了“路遇山贼”结案。
宋父一死,他的弟弟也就是宋家二伯,便联合宋家族老上门逼迫宋母收下二房家的小儿子做承嗣之人。
宋栀不知真相如何,但二伯他们不怀好意是真得不能再真,他们也确实是得利者。陈易做知县断官司时便说过,受益人大多不是无辜之人。
“娘,家里现在还和赵家镖局合作吗?”
“是呀,合作多少年了,怎么问这个?”
宋栀道:“赵叔年前没了,听说接手镖局的是二儿子?我记得赵二不是个勇猛的,以为会是赵家大哥接手生意。”
“唉,赵家大郎的那个继母厉害着呢。”
“要不让爹换个镖局走镖吧,我觉得赵二实在不行,真出什么事,他这个镖头保准比谁都跑得快。石师傅老道有经验,我看赵二不见得容得下他们师徒几个。”
是啊,他们可是一直和赵家大郎关系匪浅的,这镖师们不同心,就不可靠。
宋母十分欣慰,“你长大了,考虑事情开始比为娘周全。”
“才不是,是爹娘一直忙着女儿的婚事,顾不上自己了。”宋栀声音变得闷闷的,又想哭了。
前院西厢房里,陈易终于醒了,守着他的小厮警醒,听着点声就睁开眼,瞌睡虫跑了个干干净净。
“什么时辰了?”
“快过申时了,小姐还说您申时不醒就要小的叫你呢。”这是告诉姑爷,小姐可没有要在家过夜的意思。
陈易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也不觉得他多嘴,更不会觉得被冒犯。仆役们处处为主子考虑,是好事。
宋栀哭得鼻尖发红,一抽一抽的,但总能说话了。
宋父又有点生气,可又不好直冲着女婿,问女儿:“嫁人了还哭成这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受了多少委屈。”
“离了你们就委屈。”
在家娇养了快十七年,骤然离开双亲,一时承受不了也是有的。还嫁的那么远,夫家还穷。连个丫鬟住的地方都没有。
宋父想明白了也冷静下来,知道女儿这般大抵是和女婿本人无关,瞅女婿那一脸迷茫又心疼的样子就知道了。
否则要心虚的,他看人最准了。
宋母听了这话心更疼了,又心肝肉的抱着哄了几句。
宋父起身,叫了陈易,“母女俩都是眼泪碟子,咱爷俩可躲远点。”
陈易有些迟疑,还是宋父握着他手腕子才把人拽走,去了东厢房。
宋家家财颇丰,住的院子却不大,一是宋父为人低调,不喜张扬;二是他只有一结发妻子,一独生女儿,人口实在是少。
宋母让吴妈妈去厨房,告知晚上两刻钟再摆饭,就带着女儿回了后院。
每家女儿回门都会被母亲问上一问,“女婿待你还好吗?亲家母呢,待你如何?”
其实真挺好的。
宋栀也不能说假话,“婆母这几天给做了山药馒头,昨天下午还去了山里采野菜给带过来。”
宋母心里有数了,她就觉得王氏是个利落人。
“那我也给他们做饭了呢!”宋栀补充。
宋母最了解女儿,笑着问:“一顿?两顿?”
“娘!”
“呵呵,娘不笑你。”紧接着又问,“光说亲家母,女婿呢,女婿对你好不好?那个册子......”
宋栀声音更大了,脸刷得就红了,“娘!”她是重活一世,加起来都活了快五十年,可在母亲面前提那事怎么好意思?
她其实不太记得之前母亲是不是问过一样的问题,却想起了前一天晚上。怎么就挑那个时间回来,可真够丢人的。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娘同你讲,这事上好,别的都容易好。食色,性也,娘不唬你。”宋母看着女儿红苹果一样的脸,就知道坏不了,又忍不住逗自己的小闺女。
“别的呢,对你还体贴?”
“哼,有什么体贴的,是每天都把洗脸水洗脚水端进屋了,衣裳我瞧着也是他洗的,这活儿翡翠还做不了吗?”还不是因为陈家穷,地方小,一个丫鬟也养不起住不下的。这话太刻薄了,宋栀说不出口。
听到这里,宋母才真/觉得安心了,这说明女婿是真疼女儿,还有心。
她手上拍了下宋栀后背,把人往怀里抱,“你可真是我的小祖宗,女婿一个大男人,还是读书人,读书人清高,都愿意伺候你了!你呀,就是嘴不好,心里头是不挺受用的?”
宋栀不说话了,伸出胳膊环住宋母的腰,一个劲儿地蹭脑袋。
耍赖撒娇。
宋母见状也不再说了,静静抱着女儿,直到吴妈妈敲门,说是到时间该用饭了。
宋母带着宋栀一进前厅,就发现女婿紧往女儿脸上看,担心紧张的模样,和当年她哭后宋父的样子没有区别。
“阿栀不懂事,让女婿见笑了。”
“岳母言重了,是小婿做得不好,让阿栀受委屈了。”
本来就是客套话,陈易的回答让宋母满意,“饿了吧,赶紧坐下,先喝碗鸽子汤,加了茯苓,炖了一上午呢。”
说着,也不用别人动手,亲自给陈易盛了一碗,陈易忙站起接了。
先给陈易盛的呢。宋栀不高兴,就说:“你安心坐着行不行,一会起来一趟,饭还要不要吃了?”
后背又挨了一下。
“娘!”宋栀非常不高兴。
“女婿你可真要多担待她,就是嘴不好,心里其实是好的。”宋父也服了女儿的这张嘴,赶紧把汤勺塞进了陈易手里。
宋母也说:“她这是嫌我先给你盛汤呢,嫁人了还跟孩子似的。我就这一个宝贝,她受不了我疼别人。”
“你呀,”把鸽子汤放到宋栀跟前,用手指点她额头,“和女婿争就算了,有了孩子还和我外孙争?”
陈易嘴角挑着,慢悠悠喝汤,显然是被自己的小妻子可爱住了,待想到两人的孩子,人更柔和了几分。
殊不知宋栀正邪恶地想:外孙?呵,等我给你们弄回来个姓宋的大乖孙!
饭桌上气氛轻松起来,谁也没注意宋父一杯一杯灌陈易酒,陈易自己也没察觉。
等陈易脸发红了,突然一个劲儿和宋父说多谢,他口齿不清,有点大舌头。母女俩才反应过来。
宋母埋冤宋父,“女婿是读书人,可别喝坏了!”
宋父量大,“没多点,这是个一点喝不了的。喝坏?要是那么容易喝坏,说明身板子不行。坏了正好再给闺女换一个!”
“我看你是醉了,说得什么浑话!”宋母被吓了一大跳,赶紧去看陈易,见他没什么反应才放心。
宋父说:“女婿醉了,正好晚点走。”
宋栀没想到是为了这个,有些哭笑不得,“本来就要晚些走的,陈易应了的。”
宋父:“......那怎么了,陪他老丈人喝个酒,怎么了?”
瞅瞅这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狡辩的样子。宋母没眼看,叫两个小厮进来把女婿扶进了西厢,又让女儿进去给他擦擦脸和脖子。
宋栀震惊,什么?让我伺候他!
宋母的夫妻相处小课堂又开始了,“这夫妻之间啊,都是互相的,他疼你,你也得......”
宋栀投降,钻进了西厢。
榻上男子有些不老实,手一直扯衣领。宋栀凑近了看,陈易的额头上脖子上薄薄一层细汗。
他白,喝酒上脸的厉害,偏也不是红通通的关公模样,是淡淡的粉,很有些柔媚可欺。睫毛也长,像袖珍羽扇,宋栀没忍住上手揪了一根下来。
她抿抿嘴,拧干浸湿的帕子往他脑门上贴,然后开始擦,动作一点不温柔,堪称粗鲁,“你好命,让我伺候你。”
“看在你哄我爹娘高兴的份上。”
西屋渐渐安静下来,东屋里头陈老汉和王氏在低语。
陈宛睡得香,冒了一脑门汗,王氏给她抹干净汗后又用手背去碰她红扑扑的脸蛋儿。
还是没忍住把小女儿耳朵上的两粒金丁香摘下来。
看王氏把它们放在帕子里包了又包,陈老汉笑话她:“就知道你不能让小碗儿那么戴着。”
王氏不觉得被笑话,“你这老鬼吃了顿好饭就骨头沉了是不?小碗儿多大点,还能把金子戴耳朵上?”
太招眼了,就跟前两天她那三儿媳妇头顶上的金步摇。
我的乖乖哦,一晃一晃的,比天公老爷都刺眼!
提起这个,王氏小声说:“老三媳妇也挺懂事。这不今天就没戴?才嫁人,戴两天新鲜,也正常。”
她不知道宋栀今天戴的桃花粉玉簪更值钱,陈老汉也不知道。
“老三媳妇出手就是鸡蛋金子,晚上还有野鸡汤,我看你这老太婆是被哄住了。”陈老汉并非挑拨婆媳俩,就是觉得自家老婆子真能变脸。
田里干活时还憋了一肚子气,耕牛一样埋头苦干,干得比他都快。这才过了几个时辰,都开始给老三媳妇圆了。
“哼,你知道我不是。”王氏没再多说,把装了金丁香的帕子塞进箱柜底下,就要睡了。
但没睡着。
“儿媳妇手艺不错。”
陈老汉害怕自己老婆子找事,提问:老娘做的菜难吃是吧?于是保持沉默。
“老头子?”
陈老汉迷迷糊糊:“嗯?”
“下午我不去地里了,明天儿媳妇回门,得备些礼。”
午觉醒来,东屋门窗紧闭,王氏在炕上扒拉家里的铜钱袋子。
分家后,明面上分得十二两银子,他们老两口也攒了一两半的私房银子,一共就是十三两半。
十三两半的银子,还有一间房,要不是老三读书,这日子其实挺好过。就在她开始为将来发愁的时候,老三年后中了秀才,又被选为了叫什么廪膳生员的。
什么生她不懂,就知道是老三念书好,知道有钱有粮食拿,一个月有两钱银子加上半石的米。
才有点笑模样呢,老三就带回来一个说不清是好是坏的消息。
娶妻肯定是好的,就是这妻竟是县城里宋员外家的独生女儿。宋员外她知道,农闲时挑菜去县城里走街串巷,县衙边上的一处宅院就是宋家。
但王氏第一个反应是愧疚。
老三快十九了,老大老/二这个年龄的时候,孩子都在媳妇肚子里了,到他这却是连个媳妇的影子都没有。
王氏可不记得小儿子多花的学费纸笔钱。
读书明理,当初每个儿子都送去前山村老秀才那里读了几天书,偏只小儿子被留了下来。
儿子是读书的料,做父母的还能不理会?哪个乡下老妇不想做宰相娘?老/二媳妇不也是为着这个闹腾?
至于这桩婚事,自己生的孩子自己懂,明知在聘礼上会有些为难家里还开了口,那就是真喜欢真想娶。
县令夫人做媒人,王氏也没有士农工商的弯弯绕绕——吃饱肚子才几个年头,还瞧不起富贵商户?而且正如儿子所说,将来若真有考取举人功名那一天,有个有钱的老泰山,也不必为了赶考的盘缠银子给旁的地主豪绅多好得脸色。
她听说过,邻县头些年出了个举人老爷,中举的好消息传到家门的同时,三五个富贵员外就带着银两田地和貌美丫鬟登了门。
当时让多少人羡慕啊,一传十十传百的,结果没过上两年呢,那举人身上的功名竟被撸了干净。似乎是为着他身上挂着太多地主的田地,能免税赋,让朝廷收不上来钱了。
当时她就想了,商人多精怪,还能白给你银子不成。
可老泰山会。
宋员外家人口简单,本人名声也不错。
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王氏节俭到抠搜,在大事上却绝不含糊,第二天就回娘家把三两银子的欠账要了,手头上就有十六两银子。
十两银子做聘礼,算是图个十全十美;三两银子办个有三个大荤的酒席,儿子中秀才多长脸的事。娶妻立业,双喜临门值得把肥鸡鲤鱼和肘子都摆上桌。
二两银子给全家老小都做身细布衣裳,半两银子置办些新的瓷碗筷子。
王氏又算了一遍算过无数遍的账,再次确定手头上确实就剩了不到二两银的散钱。
老大和老/二的媳妇都是前后村的,家里过得不如陈家,二两银子的聘礼是半文没带回来不说,嫁妆不过一身新衣裳和两条薄被。凡事都讲究礼尚往来,说是回门礼,叫俩儿子切上两斤猪肉带回去添个菜都算礼重,老三媳妇这边,还真让王氏有些头疼。
八抬装得满登登的嫁妆,雕花木床都是娘家送过来的,为了全陈家脸面,只说是儿媳妇认床。更别提还有现银二十两。
这是明面上的,背地里肯定给了更多。
不是她算计惦记。
她可是秀才娘,自有点傲气在身上,才不会见天儿想着怎么搜刮儿媳妇的嫁妆。
将心比心,假说她要是有那么大一份家财,等小碗儿出嫁那天,非得陪上自己半数私房。这还是因为小碗儿不是独女,否则全家不还都是她的?
一家人分不清,再说不用儿媳嫁妆,天长日久下来,肯定是他们占便宜。等儿媳妇生了孩子,更不用说了。
便是眼前的,今天午饭后她给了小儿媳妇五十文,也被退回来十文,儿媳妇只收了野鸡的钱。
唉,穷就是穷。
王氏琢磨来琢磨去,把钱袋子收起来,出了屋。嘱咐了几句陈宛不要乱跑,就拎着背篓,往山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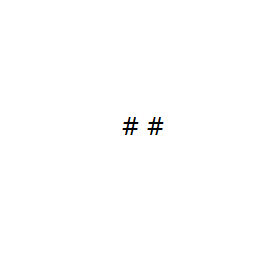
最新评论